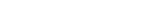新闻动态
作者:小编 发布时间:2024-06-13 02:48:33 浏览: 次
半岛综合体育赵树冈: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李亦园的宗教人类学研究【摘要】李亦园先生(1931-2017)是著名人类学者,研究领域包括少数民族、海外华人,以及汉人社会与文化。长期致力宗教人类学,同时对中国典籍与民间传说神话有浓厚兴趣,着重以行为象征与结构探讨中国民间文化的核心元素,毕生追求目标在于探究“中国文化的全体”。综观李先生的中国民间宗教与民间文化研究可以发现,他除了从各类传统文化的表象,诠释民间宗教与仪式的内在逻辑,尝试理解中国文化内在核心概念,同时以人道关怀的立场,透过日常实践发挥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
1949年前后从中国迁徙到的知识分子都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并承继了五四反传统、反迷信,大多对民间宗教和民俗研究兴趣不高甚至排斥。在接受日本教育的同一世代知识界也以类似心态看待民间宗教活动,而少数被视为民俗学的前辈学者,大多单纯记录保存或利用史学考据,尝试追溯这些活动的起源。李亦园先生的教育背景和第一代来台的知识分子类似,在故乡泉州华侨中学完成学业,1948年入大学,师从李济之、凌纯声等中国第一代人类学者。在接受完整的人类学训练又赴哈佛求学,因此兼具中西方学术视野,在理论与方法上也与早期接受日本教育的民俗学者有较大差异,更着重从中国文化整体脉络思考民间仪式。
李先生在大学人类学系讲授宗教人类学课程数十年,发表大量中国民间信仰、传统民俗与仪式的学术或通俗作品。由于学术专长与声望,长期受邀担任省民政部门对民间信仰与习俗的政策研究。他不断强调“传统文化”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更借此与学界对话,希望“研究中国‘大传统’文化的同仁也能注意到一般人民大众的生活文化,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欲,因为无论如何,他们生活的一切也代表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欠缺对这些常民文化的了解,总是难于窥视我们中国文化的全体”。[1]李先生的学术生涯经历了俗民文化研究从边缘到兴盛的转折,他透过民间信仰与仪式行为分析,探讨传统文化的本质与意义,更透过个人实践,彰显中华文化的价值。十九大报告相当突出中华传统文化,而中华文化除了浩如烟海的典籍,璀璨的艺术外,也不能忽视着重生命关怀、天地人和谐的民间信仰与仪式,这些民间文化同样是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传统习俗当中对礼与秩序的追求也相当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1950-60年代的结构论、象征论是人类学界的主流,尤其是宗教研究领域,学者除了探讨宗教的功能,更希望从复杂的过程中分析仪式行为、各类人与物的象征,宗教现象的内在结构,及其反映出该信仰者的宇宙观。李亦园先生从中国民间宗教到中国文化整体的探索,除了人类学理论外,主要是联结了杨庆堃的宗教分类以及杜维明对“文化中国”概念的讨论。
李亦园先生非常推崇杨庆堃中国宗教研究提出的“制度化宗教”和“普化宗教”。虽然这个分类已经从学界耳熟能详普遍接受,到现在遭受二元区分和过于简单的批评,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中国民间宗教确实与全国一致的节日,家族祭祖、扫墓,或各地特殊的禁忌与仪式等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事实。各次宗教统计调查发现,佛教、天主教、教、伊斯兰等信徒相对较少,大多选填道教或是无宗教信仰。但进一步分析,选填“道教”的民众大多不是宗教学者定义的道教,他们和选择无宗教信仰选项的民众类似,在特定时间进入寺庙进行祈福、除秽等仪式,同时在每年的春节、清明等节日烧香、烧纸。这类绝大多数选填“道教”或“无宗教信仰”的民族和海外华人都践行着所有中国人惯常的仪式行为,但这些仪式却无法归类为任何宗教,这也是杨庆堃用“普化宗教”(diffused religion)一词描绘中国民间信仰最重要的原因。
杜维明曾经从文化探讨中国这个的概念,认为中国、、香港、新加坡构成文化中国的第一层,海外华人构成第二层,学者、记者以及文学作者观念中的中国则构成文化中国的第三个层次,透过这三个象征世界(symbolic universe)探讨文化中国。[2]李亦园认为,杜维明的“文化中国”提供了从大传统,平面的角度理解中国的架构,如果要更全面的探讨这个概念,有必要从垂直的角度理解庶民生活,从民间文化的角度分析形成中国文化的普遍价值观。透过累积大量的中国民间信仰与仪式、家庭制度的研究基础半岛综合体育,李先生总结了“三个层面和谐与均衡致中和”观点。三个层面包括:代表自然系统的“天” (时间与空间的和谐),有机体系统的“人” (内在与外在的和谐),人际关系的“社会” (人间与超自然界的和谐)。从这三个层面整体的致中和观点诠释中国传统当中的个人、社会到自然所追寻的和谐均衡最高目标。[3]从时间来说,致中和三层面和谐与均衡是贯穿中国数千年的宇宙观,从空间来说,还扩展到各地海外华人圈,使得全球海外华人同样延续了食物属性的“凉”与“热”,个人八字、出生生肖与流年的“冲”或“合”等观念。[4]
无论是杨庆堃的“制度化宗教”和“普化宗教”,还是“大传统”与“小传统”,或是类似人类学早期“民族性”研究对“中国文化”的讨论,已经不再是学术研究的主流。但是就学术史与时代脉络,还是相当值得思考为什么包括李亦园先生在内的同世代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心理学者杨国枢、学者胡佛、社会学者金耀基、杜维明等,不断思考社会科学中国化,以及从中国社会文化现象提炼出中国特有,且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概念。这些前辈学者进行研究的基本前提是,无论“中国文化”的定义是什么,首先要说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确实有一个绝大多数人认同,有别于其他社会,属于中国人共同遵守的行为典范或法则,其次是研究者自身也具有高度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感在当前的社会环境更为重要,如果缺乏文化认同,其他凝聚中国为整体的概念将失去内在生命。
汉人或海外华人社会的宗教人类学和民俗学、宗教学,甚至历史学的中国民间宗教在研究对象与内容上有时很难发现区别。研究中国宗教的汉学家很可能对仪轨、及法师的师承感兴趣,宗教人类学和民俗学不是不关注这些问题,而是将焦点放在仪式的象征与当下的社会意义。但无论民俗学、史学、人类学以及欧洲汉学界大致形成了共识,要理解中华文化或道德伦理的日常生活实践不是透过士大夫或知识分子,而是流传在民间,种种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戏剧与仪式等民俗活动。[5]宗教人类学和民俗学讨论的往往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信仰现象和仪式,中国民间宗教也无法用西方宗教理论加以定义,因为民间宗教是渗透到日常生活,同时也和命理、风水、中医、饮食等观念密不可分。
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底层社会的迷信与愚昧无知主要在于贫穷和知识水平低下。然而,随着196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发展与平均教育水平都明显提高的社会背景下,各色各样的民间宗教活动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更为兴盛。从几次大规模的宗教调查发现,天主教、教、佛教等“制度化宗教”的信徒没有成长,反而是民间信仰的庙宇数量不断增加,而整个趋势又和工业化、商业化进程同步。由此可见民间信仰现象不是简单的教育和经济可以解释。如何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急遽变迁的时代背景理解中国民间信仰与仪式,早期经济快速成长背景下的民间宗教仪式与新兴教派的发展过程成为值得研究的案例。
李亦园先生在宗教人类学的理论基础上,讨论中国传统宇宙观以及民间信仰,进而论证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与其现代化的适应着力颇深,针对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伴随而起的民间宗教现象,他主要以“功利主义”和“道德复振教派的兴起”两种趋势进行分析。[6]透过分析民间宗教与现代化发展过程,李先生提出民间宗教信仰与仪式在经济发展过程的作用,发现传统民间信仰不仅与工业化、现代化并行不悖,蕴含其中若干功利、实用和积极的因素反而在民间社会或“小传统”中发生作用,也有可能是经济发展的潜在根源。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等社会学者曾经尝试以儒家伦理诠释东亚的经济发展,认为儒家传统的制度与规范,成功转移到现代公司、工厂组织或制度,但接受李亦园先生论述民间宗教信仰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现象后,加入民间文化因素,以“世俗化的儒家思想”(vulgar Confucianism)解释东亚地区的现代化。[7]金耀基认为,“世俗化的儒家思想”不见得完全诠释了东亚现代化发展,但文化对经济现代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8]
工业化或现代化并没有使得传统的宗教信仰与仪式消失,甚至在功利主义的追求下,讲求个人的、即时性的仪式更为兴盛发达。[9]日常生活的仪式行为究竟是民俗还是民间宗教是不大恰当的命题,如果我们持续以西方宗教学的定义界定中国民间宗教,将中国传统上属于生活的仪式排除在日常之外,永远无法认识中国社会的本质。民俗活动与民间宗教仪式的意义还是需要回归日常生活,回归传统文化脉络,而李亦园先生也充分发挥了民间信仰的日常实践。
的民间信仰活动异常丰富多样,虽然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和政府都曾经试图禁止或劝导,但成效似乎不大。[10]全台各地大大小小的寺庙非常密集,家庭式宫庙也充斥在大街小巷。至少在90年代以前,这些信仰与仪式在社会主流媒体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眼中,还是将其视为落后愚昧,更难与学术殿堂联系起来。各类媒体也经常刊载宗教活动的铺张浪费以及相关的负面新闻,的宗教主管部门对这个现象十分关切,采取诸多劝导措施,学者们也纷纷投书,要求各单位制定相关因应政策。
中国民间信仰形态非常复杂,也正因为如此,宗教人类学在中国社会更能发挥深入理解当代宗教现象,维系社会整体运作的贡献,也较西方一神信仰的社会更具实用性。[11]李亦园先生长期关注文化变迁与传统的现代适应问题,早在1978年即出版了《文化变迁与现代生活》,以深入浅出的笔调,用人类学者的观点分析的文化现象,也不断在学术与通俗媒体论述现代生活中的民间信仰与仪式。[12]因为研究领域和声望,多次主持省民政主管部门有关民间宗教的课题和会议。站在省政府立场,主要是希望学者与宗教界人士对民间宗教仪式过程的浪费、烧纸燃炮导致的环境污染与噪音问题提出改善建议。李先生也以民间宗教研究的学术背景,分析仪式行为的象征等问题,提出人类学者的回应,同时针对宗教仪式的改善标准提出建言。其中最具体的建议是希望以示范取代僵化的禁令,以及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观察民间宗教与民俗活动。[13]
清华大学社会与文化学院的兴建过程曾经被高度关注与报导,充分反映出社会对学术与民俗活动的观感,而李亦园先生也透过这个过程表达与实践了他对民间仪式的态度。清华大学位于新竹市,1980年代规划的社会与文化学院院址坐落在校园边角,一处名为“梅谷”的坡地。此地自清代以来就是坟场,到国民政府来台后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坟头。直到1987年动工前,还有为数众多的坟冢没有后人处理,新竹市政府在公告期满后,依法将这些坟悉数迁出。为了安抚工人情绪,担任院长的李亦园先生准备馨香、素果,并手书祭文,在仪式结束唸祷后焚化。李先生告诉工头:“我是学宗教的,也教宗教,对于宗教我有基本立场,举行拜拜的仪式是希望能安慰他们。”这里所说的“他们”可以有两层意思,表面的意思是使工人心安,另一层更重要含义是对这些无主骸骨的尊重。
学院兴建过程的琐事应该不需要享有中研院士学术声望的院长出面,李先生亲临献祭的过程也和如同一般所见的清明墓祭。如果这个仪式是迷信,全国普遍奉行的清明扫墓或许也将列为迷信。虽然不同时代与区域对骸骨有不同处理方式,除了极为少数的特例,对于逝者的尊重几乎是人类社会的普同价值。[14]中国历史上对无主枯骨表达尊重的仪式可以从《礼记》发现“厲祭”的记载,也可以从历代文献看到官方的实践,各地处理无主枯骨的仪式虽有地区性差异,但以馨香、素果致敬应该是最常见的方法。[15]流传千古的《瘗旅文》,描绘了贬官贵州龙场驛的王阳明安葬客死他乡的陌生吏目子仆三人,除了葬之、祭之,也撰祭文以悼之,反映出一代文人、道德表率的人文关怀。
1990年新院馆落成时,李先生已经离任,由王秋桂教授任代理院长。王院长长期负责著名的《民俗曲艺》期刊,也主持过全国8个省份的戏曲仪式大型研究,对传统戏曲与仪式有着浓厚兴趣。在学院新院馆落成启用前,特地按习俗举办了一场“入厝”(按:闽南语的搬新家)仪式。王老师告诉我,当时除了举办了隆重的道教科仪,还特别请了宜兰林讃成先生著名的戏班,以提线木偶操办了“跳钟馗”。[16]清华大学前后任两位院长举办民俗活动被媒体大幅报导,认为两位院长提倡迷信。事实上,类似的仪式在非常普遍,尤其是“跳钟馗”在每年开庙门更是不可缺少。这个例子显示出,的民间信仰并未遭受强烈禁止,但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相当排斥。对于长期从事宗教研究的李先生来说,这起事件使得他更积极向社会大众解释仪式与迷信的差别,从人类的行为结构,论证仪式与迷信的分别。
无论复杂的道教仪轨或简单的上香献花,都是一套外显行为。李亦园认为,行为除了表面意义,还有其三个深层结构层次范畴,分别是实用行为 (practical behavior) 、沟通行为 (communication behavior) ,以及巫术行为 (magic behavior) 或崇奉行为 (worship behavior)。他以我们日常所见端起茶杯为例,生动的说明了这三类行为。当一个人因为口渴,举起茶杯喝茶,此一行为是实用行为。同样端茶杯,但主要是向坐在对面的人示意,此一行为就未必是实用的了,可能是邀请坐在对面的朋友喝茶,也可以是表逹敬意,有时甚至是示意“端茶送客”。这时端茶的行为就不是单纯口渴,而是具有特定含义的沟通。如果双手端了茶(或酒)向神像或任何宗教象征,甚至苍茫的天空表示敬意,这一行为就更没有实用意义,只是表达对超自然的崇奉行为。沟通行为和崇奉行为又称为仪式行为,所以仪式只是一种形式,不一定其有实用目的。仪式又依其作为人际关系或与神的沟通,分为世俗和神圣两种,都是一种藉由行动表达意愿的行为。
透过行为分析的仪式本身就没有迷信或不迷信的问题,重点在于进行仪式者的意念,“假如做仪式只是一种象征行为,以求心安而已则不能说是迷信;然而把它当作真的有实用意义,那就是迷于仪式的象征原义而信之,则是迷信了。”[17]李亦园先生不断在学术期刊或通俗媒体表达的重点主要是民俗与迷信不能画上等号。对于“迷信”或“非迷信”的界定不仅是针对社会大众的呼吁,更是对针极端反传统,视民间文化传统如糟粕的各类学者。李先生之所以强调所谓“迷信”或“非迷信”的区别,还在于他对中华文化的总体关怀。诸子百家、经史子集是中华文化,我们日常生活中被民众接受且流传至今的风俗信仰同样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以行为分析等方法研究民俗,同时区分学术意义的仪式与实际信仰观念上的仪式,进而探寻仪式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
现代社会的信仰仪式表现在戏曲最为明显。姜士斌(David Johnson)认为,仪式与戏剧在中国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二者有不可分的渊源关系,都是借由行动表现意义,“因为中国人的道德是借由行动表达,道德伦理不是理论的存在而是实践的行动。意识和戏剧对中华文化的意义就在于传递了实践文化精神,将生活经验与理想借由行动表现出来”[18]。现代化传播媒体普遍进入日常生活以前,根植于文化底层的理论架构透过戏曲等方式传播,一方面可作为士大夫或儒者安身立命的哲学依据,同时也成为一般民众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但在变迁时代中,这些理论架构或行为准则很容易趋向于现实生活的适应,尤其一般民众更容易朝向现实功利态度的转化。李亦园认为,姜士斌在《仪式剧与戏剧仪式》书中,对戏曲、仪式、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进行深入的论述,他的《目莲救母》传统剧目分析也为中国戏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由于姜士斌研究的结论提及从戏曲很难发现中国的共通价值,使得李亦园延续姜士斌以及其他汉学家共同认为中国文化当中仪式与戏剧不可分的角度,同样以《目莲救母》戏曲为例,从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的信仰观念探讨中国戏曲的和谐与超越。[19]这个研究的意义在于,当我们观察经常与“迷信”产生联想的戏曲与仪式,重点应该是分析这些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和文化意涵,也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进一步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与象征。
中国民间宗教关键的特质是“神圣”与“世俗”没有绝对界限,信仰与日常生活高度结合,中国地方戏曲除了作为大众娱乐,经常也具有酬神的意义,兼具娱人和娱神的功能。当前各级政府对中华文化的传承非常重视,也不约而同的试图透过民俗活动或各类民间技艺发展地方旅游。如果我们认同各类戏曲具有传递与实践文化精神,将生活经验与道德理想透过行动展演的意义,推动各类民俗活动不仅对经济发展有利,更有助于中华文化伦理价值观的传承与推广。然而,许多中国戏曲仪式有属于世俗的娱乐一面,同时更具有丰富文化意涵的一面,在传承的过程中除了技艺,更需要传承的是深层的文化意涵。例如,泉州提线木偶因为演出技巧高超,表演活灵活现,不仅经常穿梭两岸,也远赴世界各地演出,非常适合用来说明民间文化的技艺及其内涵的传承。
1999年底至2000年初,泉州木偶剧团应邀参加在举行的“中国少数民族博览会”,在汉族的展示区演出。李亦园与王秋桂教授与这个剧团十分熟识,嘱咐我在演出期间的农历正月十六参与。因为当天为相公爷诞辰,该剧团特别演出难得一见的“大出苏”。相公爷即傀儡戏班守护神--田都元帅,该神亦有田府老爷、田公元帅等别称,相传相公爷幼时被苏姓人家扶养,因此相公爷出棚又称为“出苏”。虽然这场仪式是夹杂在当日的例行演出,但演出者在仪式开始前对观众强调,大出苏是一场庄严的仪式,绝非一般性的表演,请所有观众于仪式进行间,切勿喧哗或鼓掌。观众在整个仪式进行中相当配合,不仅欣赏到难得一见的大出苏仪式,同时也融入了整个仪式的氛围。
相公爷除了“看起来很自然的就是傀儡戏神”外,他的音乐才华和调兵遣将的能耐,也使其成为民间戏曲界及狮阵、宋江阵等技艺界普遍信仰的神明。[20]有关田都元帅的传说相当丰富。其中较常见的就是将其比附为平定安史之乱有功的大将军雷海清,或是雷海清的兄弟,与张巡、许远死守睢阳,后遭乱箭射杀的雷万春。[21]对道教仪式与文献有深入研究的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不赞同以上的观点,认为这些说法都显然荒诞不经,他从中国民间信仰与《道藏》里纯道教仪式的比较,论证傀儡戏班供奉的三戏神就是《搜神记》风火院田元帅三神,而田都元帅即为三元帅中的大王爷,也就是田都和合元帅。[22]丘坤良则认为,做为近世戏曲之神的田都元帅系混合了各种宗教、戏剧历史传说的结果,其角色与宋代以来的清源祖师极为接近。[23]
在此暂且不论田都元帅种种考据,至少从海内外的汉学家和宗教研究者可以了解傀儡戏在热闹的演出外,背后还有极为丰富的文化意涵。提线木偶与各地的剧种,除了一般人看到的娱乐性,更有其作为民间宗教活动至为关键的仪式性。如大出苏仪式除了用以庆祝相公爷诞辰外,也是傀儡戏演出前的必要仪式,过去较富裕的人家逢乔迁或吉庆时,也会请剧团为其本宅举行大出苏,以镇凶煞、延吉庆,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一环。对研究者而言,仪式剧与仪式的界限是难以区分的,甚至是相互融合为仪式表演(ritual performance),就远离信仰脉络的台前观众来说,吸引他们的绝不会是仪式的象征意义,而是相公爷木偶曼妙的舞姿,震天的锣钹唢吶和贯穿全场的“啰哩连”。
提线木偶是传统文化非常精妙的表现,观众很难想象几根丝线操控的木偶可以演出诸如执壶倒酒精确入杯的细节,因此这种演出无论在国内外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也毫无疑问属于需要传承的宝贵文化遗产。然而,在表演形式以外,我们也可以发现上述国内外学者对整个剧种仪式性的探讨。站在学术研究的立场,除了演出技巧的传承,更有必要在民间信仰的角度,深入探讨民俗曲艺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民间信仰与戏曲作为传统道德伦理的文化行为表达形式,如果在追求经济利益,完全强调戏曲仪式的娱乐效果,以各类荒诞无稽的情节吸引外来游客,甚至委托音乐舞蹈专业人员重新改编,进行“非遗”申报半岛综合体育,将原本紧密与生活结合的仪式硬生生抽离,将对文化传承带来负面结果。从民间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而言,传统文化的土壤在日常生活,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日常的践行,除了要反对一切借由民俗或民间宗教名义敛财或扰乱社会秩序的乱象,更应该制止一切以传统为名,为各种利益虚伪造假的“伪民俗”活动,让民间信仰回归日常生活。
李亦园先生两年前刚过世的前几天,来自各界的师友纷纷前来吊唁。有位社科院的友人快到灵堂前,突然问了我:“李先生是信仰什么宗教?”我这时才发现,和李先生无数次的谈话过程虽然论及宗教人类学和民间信仰等问题,但从未问起李先生自己的宗教信仰。只记得李先生曾提起,研究宗教是否要有某一种特定信仰似乎有些难于抉择。如果没有信仰特定宗教,如何能有深入的体悟?如果成为某特定宗教的虔诚信徒,在进行研究时又如何保持中立客观?李先生长眠在的佛寺,但我知道这是李师母和儿女共同的选择,不能以此论断李先生是佛。从李先生生前不断受邀与佛教、天主教、教、道教,以及民间宗教社团的对话中可以理解,李先生对所有宗教都没有分别心,而是站在中华文化整体视野,寻求民间信仰的时代意义。李亦园先生对宗教人类学的贡献与其说是运用,不如说是他透过亲身实践,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均衡透过日常生活实践。
[5]何建明主編《道教學刊》2018年第一輯,總第1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第3-12頁。
[6]李亦园,《民间宗教的现代化趋势》,《中国宗教伦理与现代化》。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
[8]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杨国枢、李亦园、文崇一编,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页29-55。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5。
[9]李亦园,《民间宗教的现代趋势:对彼得柏格教授东亚发展文化因素论的回应》,《文化的图像》(下册),页117-138。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1。
[11]李亦园,《宗教人类学的实用性》,《人类学与现代社会》,页57-65,台北:水牛出版公司,1992。
[13]李亦园,《民间宗教仪式之检讨—讨论的架构与重点》,《民间宗教仪式之检讨研讨会论文集》,页1-7。台北:中国民族学会,1985年。
[14]中国历代的墓葬制度与观念参阅蒲慕州的《墓葬与生死-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3年。
[15]林富士,《孤魂与鬼雄的世界:北的厉鬼信仰》,新北市:新北市政府文化局,1995年。
[16]李亦园先生是我的导师,王秋桂先生是我修读中国民俗学的老师,有关清华大学社会与人文学院馆院兴建的相关活动主要来自二位先生口述。另见《民间戏曲的文化观察》,原载《联合报》,1993年2月5日。
[17]李亦园,《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仪式》,《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页73-91。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5年。
[19]李亦园,《和谐与超越—中国传统仪式戏剧的双重展演意涵》,《民俗曲艺》2001年,128期。
[20]龙彼得 (Piet VanDer Loon),《中国戏剧源于宗教仪典考》,《中国文学论著译丛》(下),王秋桂、苏友贞译,页540-541。台北:学生书局(1985)。
[21]郑正浩,《乐神一考:的田都元帅和西秦王爷信仰》,《民俗曲艺》23-24(1983),页118-140。吴文理译。
[22]施博尔(Kristofer M. Schipper),《滑稽神:关于傀儡戏的神明》,同上揭书,页106-117。萧惠卿译。
[23]邱坤良,《的傀儡戏》,《中国文学论著译丛》(下),王秋桂、苏友贞译,页1-24。台北:学生书局,1985。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深圳某老牌地产公司3小时裁掉所有员工?前员工称“未办任何工作交接”,官方已下达整改通知书,办公现场已无对接人
欧盟即将对华电动车加征最高25%关税!德国反对:我们的BBA受冲击最大半岛综合体育,去年中国销售480万辆汽车
《真·女神转生V Vengeance》评测:1+1=2/
主站 商城 论坛 自运营 登录 注册 《真·女神转生V Vengeance》评测:1+1=...
Copyright © 2012-2026 半岛·综合体育(中国)官方网站-BANDAO SPORTS 版权所有 备案号:琼ICP备19001325号-1 HTML地图 XML地图txt地图


















 您当前的位置:
您当前的位置: